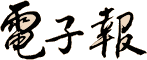從非虛構到老年影像——專訪羅福林(Charles A. Laughlin)教授
學人動態
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電子報第66期
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電子報第66期
2020-04-25

從大學生、助教到學者的學思歷程
就讀於明尼蘇達大學的時光,是羅福林教授開始接觸中國文化的開端。回想起當時所受訓練,雖然不一定是相當系統化的課程,但也有四年的現代漢語課程、一年的文言文課程,以及文學作品選讀。當時在上完四年漢語課後,有所謂「五年級中文課」,選讀中文文本,而且一般是文學作品如散文等,這使得當時學習中文的美國學生,得以通過選讀文本積累對中國文化的初步認識。不過,這種選讀課正在逐步消失,由於許多上完四年級語言課的學生,無法銜接上第五年的選讀課程,因此目前大概只有常春藤盟校及一些主要的州立大學還保持這樣的課程設計。不過,由於曾在1985年至天津南開大學上過中文暑期班兩個月,大學三年級時又到南開大學交換一年,因此已經開始具備閱讀三言二拍等中國傳統小說的能力。返美後,在漢學家Richard Mather(馬瑞志)的課堂上繼續學習文言文課程,在馬瑞志重視文本感覺的訓練下,奠定了中國文化的知識基礎。
博士班時期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延續著本科時期對於中國現代文化與文學理論的興趣構思博士論文。當時系上要求中文專業的博士生都必須修讀日語,因為古代中國漢學研究有許多重要著作皆以日文撰著,因此羅福林教授也學習了三年多日語。除了課程外,博士生也必須和教授合作授課,當時哥大要求中文專業的博士生,要配合另一區域的教授共同教授東亞文化課程,因此羅福林教授也曾與日本研究的學者共同授課,從中累積了重要的教學經驗。
從報告文學、小品文到紀錄片
當時完成博士課程後,由於夏志清教授已經榮退,王德威教授則剛被聘入哥倫比亞大學,因此就有了許多向王老師討論的機會。原本將研究主題設想為中國現代散文的羅福林教授,經過與王德威老師的建議,開始著手於報告文學的研究。
從20年代末就開始醞釀成熟的報告文學,參與了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發展,也可以從中觀察作家們如何將文學,視為改造社會的工具或手段。事實上,報告文學是全球化的現象,在共產國際推廣、外傳後,又通過日本報告文學的翻譯及介紹傳至中國。當一個作家參與報導文學的寫作,實際上就參與了全球的國際革命性運動。
不同於早期具有批判性與鋒芒,49年後報告文學在文類上雖然保有崇高地位,但是批判性卻由於政權更替遭到閹割,轉而歌頌黨與革命。雖然如此,報告文學仍然具有許多理論意義,因為對於讀者而言,「報告」仍暗示真實性。然而,一種藝術形式如何能包含真實性?真實性的力量從何而來?
這其實和小品文是有關係的。因為,籠統而言小品文也是非虛構寫作,也有它的真實性,說得更進一步,其實除了小品文沒有別的散文。當然,我們可以指出周作人、林語堂的風格姿態,更像是小品文。但是翻開現代文學史的書寫,至少在過去以英文撰寫的學術研究中,甚少提及小品文與抒情散文,在大陸的文學史也因為政治、道德等立場略過不談,這都引起羅福林教授的研究興趣。
事實上,評價小品文的重要標準之一是誠懇,而誠懇顯然是評斷真實性的價值觀,而不是科學或客觀要素。其植基在文本之中,是打動讀者的重要關鍵。從報告文學到小品文,並非是全然相異的兩種文體,而更近於光譜的不同面向,有其相似處,更可以互相觀察。正近似於此,劇情片與紀錄片與其說是全然不同的影像,不如說或多或少具有真實性。
形式與內容的繫連
「我覺得要提防的是,不能要把什麼都說成是風格與形式。」羅福林老師分享近年研究影像的心得,提及自身對於跨學科資料、老年研究的涉獵與參考,背後的動機是為了避免只是停留於抽象的形式層次,為審美而審美。一旦捨棄具體的老年議題,研究影像中的老人形象就會抽離出具體脈絡,而使得老人形象只是被影像研究消費的符號。
美感、風格及形式研究不僅不能和現實脈絡區分,也不應該和文本內容切分。形式和內容,並非二元對立,形式往往即是內容。從電影而言,就有導演會刻意使用類似紀錄片的形式,藉以帶來真實感。當然,這不是意味劇情片與紀錄片沒有差異,劇情片通過導演的控制、加工及劇本,是通過規劃的製造品,然而紀錄片沒有劇本,畫面也較為紛雜,訊息以相較混雜的方式呈現。部分獨立紀錄片導演,甚至有意追求訊息的不可預測性,並將之視為紀錄片的神髓。
如果以旁白而言,在商業或政治宣傳的紀錄片中,總是存在著強而有力的旁白,它的聲音是真理的所在,它四處存在,但是觀眾卻無法辨認聲音從何而來,為何能掌握權威。相較於此,獨立、具批判性的導演則試圖顛覆旁白。在《跳舞時代》中,旁白只是在必要的時候提供背景,介紹被採訪的人等,而影片的聲道更多是讓人物自己發聲,在聲音的混亂中,反而讓諸多主題自己呈現,由於沒有明確的主軸與引導,反而啟發觀者對於許多議題的思考。再以兩個紀錄片為對比,柴靜的《穹頂之下》討論汙染問題,偏向以旁白的聲音為中心主導,但是王久良的《垃圾圍城》講北京非法垃圾場,電影僅呈現問題的後果,卻未告訴觀影者任何解答,而只是引導觀者從影像進行反思。
談到關於一些紀錄片被批評具有感傷傾向的批評,羅福林教授認為像是《跳舞時代》就並不感傷。它固然以相當讓人舒服、讓人享受娛樂的方式,似乎只是敘述對過往充滿懷舊的故事、紀錄收藏唱片的生活樂趣等等。但是,若從政治宣傳的角度,身在殖民時期的生活,不是應該描寫黑暗、痛苦的經驗嗎?但是《跳舞時代》顯然沒有這麼做。這事實上意味著歷史經驗並不如政治宣傳一樣單一,因而也是呈現政治鋒芒的巧妙方式。古倫美亞唱片公司顯然是出於商業目的,卻也無意間培養了本土文化,因而形成台灣認同的基礎。因此電影實際上並未將問題從政治角度予以簡化,反而是呈現現向的複雜化,此中呈現的不僅是藝術價值,也同時是人文價值。
老年與遺像
在幾次演講中,羅福林教授都提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以降對於青年的推崇,並反思:與年輕的範式相對,是否也存在老的範式?不過,羅福林教授進一步說明:具體而言,這當然不是意味著五四時期或當代文化可能存在對老人的推崇。以老年人在影像中的意義而言,羅福林教授認為老年意象是批判主流商業影像的方式,是跳脫出主流審美,而提醒在消費文化之外存在的生活真實性。
老人固然不取代青年,從另一個面向而言,今日的老年人正是昨日的革命青年,特別是經歷過革命後果,成為對革命抱有遺憾的老人,自身即是歷史的化身,呈現歷史變遷,但這當然也是具有特殊時代脈絡的現象,二三十年後的老年人,也已經不曾經歷革命了。
羅福林教授對於電影中的老年研究,切入點之一是遺像。他指出,在大陸電影中目前已經蒐集到許多文本案例。遺像不一定是相片,也可能包含遺物。遺像弔詭的意義在於它見證人存在的時間,但是遺像的呈現意味著人已死去。正如同照片捕捉已失去的時間,同時是在與不在。遺像或許某程度即是紀錄片的象徵,或者說紀錄片即是遺像。
回到老年意象,如果說老年是批判主流商業的方式,老年或許意味著障礙者,因此更大的範疇是主流價值中被邊緣化的人群,因此大陸許多紀錄片拍攝了精神病患、毒癮等邊緣者的畫面。老年研究,某程度而言是羅福林教授研究邊緣影像的一個切入點。
給年輕學者的建議
「我年輕時美國的學術訓練,好像就是習慣批判主要影響的學者著作,作為研究的基礎,我覺得這個不太好,好像是以前的研究沒有價值」比起耽溺於否定前人,刻意求奇求變,羅福林教授建議研究應該以合作、不同學者跨領域協力研究為方向,會比起一味排詆前人更有意義。
對於當今學習中國文化的年輕學子而言,越來越嚴峻的問題是漢學是否還被視為是一種專業對待。專業意味著有他自己學科的研究方法,像是人類學有其方法、歷史學有其方法,然而近年美國學科的配置漸漸傾向跨學科或者跨專業發展。
漢學家的培訓的前景,在美國面臨嚴峻挑戰。許多大學不再設立具體語種、文化或區域的研究學門,像是德語文學系、義大利、葡萄牙……都越來越少。空疏不紮實的全球學在美國非常流行,而至於紮實鑽研的區域研究,現在集中在最古老的常春藤大學,才保有嚴實的亞洲學的研究,具有區域研究的研究資源與能力。如果照現在美國高教發展,漢學訓練或許會逐漸消失,做中國文化研究的可能只剩下母語中文的研究者,使人遺憾。
羅福林教授建議青年學子,應該要看世界各地有哪些地方可以紮實培訓中國文化,因為有這樣條件的教研單位,在美國越來越少。近年香港大學中的發展傾向特別有意義,因為除了華人,也有很多歐美研究者在香港做中國研究,因此呈現多元的樣態。
採訪撰稿:吳佳鴻(台大中文系博士生)
就讀於明尼蘇達大學的時光,是羅福林教授開始接觸中國文化的開端。回想起當時所受訓練,雖然不一定是相當系統化的課程,但也有四年的現代漢語課程、一年的文言文課程,以及文學作品選讀。當時在上完四年漢語課後,有所謂「五年級中文課」,選讀中文文本,而且一般是文學作品如散文等,這使得當時學習中文的美國學生,得以通過選讀文本積累對中國文化的初步認識。不過,這種選讀課正在逐步消失,由於許多上完四年級語言課的學生,無法銜接上第五年的選讀課程,因此目前大概只有常春藤盟校及一些主要的州立大學還保持這樣的課程設計。不過,由於曾在1985年至天津南開大學上過中文暑期班兩個月,大學三年級時又到南開大學交換一年,因此已經開始具備閱讀三言二拍等中國傳統小說的能力。返美後,在漢學家Richard Mather(馬瑞志)的課堂上繼續學習文言文課程,在馬瑞志重視文本感覺的訓練下,奠定了中國文化的知識基礎。
博士班時期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延續著本科時期對於中國現代文化與文學理論的興趣構思博士論文。當時系上要求中文專業的博士生都必須修讀日語,因為古代中國漢學研究有許多重要著作皆以日文撰著,因此羅福林教授也學習了三年多日語。除了課程外,博士生也必須和教授合作授課,當時哥大要求中文專業的博士生,要配合另一區域的教授共同教授東亞文化課程,因此羅福林教授也曾與日本研究的學者共同授課,從中累積了重要的教學經驗。
從報告文學、小品文到紀錄片
當時完成博士課程後,由於夏志清教授已經榮退,王德威教授則剛被聘入哥倫比亞大學,因此就有了許多向王老師討論的機會。原本將研究主題設想為中國現代散文的羅福林教授,經過與王德威老師的建議,開始著手於報告文學的研究。
從20年代末就開始醞釀成熟的報告文學,參與了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發展,也可以從中觀察作家們如何將文學,視為改造社會的工具或手段。事實上,報告文學是全球化的現象,在共產國際推廣、外傳後,又通過日本報告文學的翻譯及介紹傳至中國。當一個作家參與報導文學的寫作,實際上就參與了全球的國際革命性運動。
不同於早期具有批判性與鋒芒,49年後報告文學在文類上雖然保有崇高地位,但是批判性卻由於政權更替遭到閹割,轉而歌頌黨與革命。雖然如此,報告文學仍然具有許多理論意義,因為對於讀者而言,「報告」仍暗示真實性。然而,一種藝術形式如何能包含真實性?真實性的力量從何而來?
這其實和小品文是有關係的。因為,籠統而言小品文也是非虛構寫作,也有它的真實性,說得更進一步,其實除了小品文沒有別的散文。當然,我們可以指出周作人、林語堂的風格姿態,更像是小品文。但是翻開現代文學史的書寫,至少在過去以英文撰寫的學術研究中,甚少提及小品文與抒情散文,在大陸的文學史也因為政治、道德等立場略過不談,這都引起羅福林教授的研究興趣。
事實上,評價小品文的重要標準之一是誠懇,而誠懇顯然是評斷真實性的價值觀,而不是科學或客觀要素。其植基在文本之中,是打動讀者的重要關鍵。從報告文學到小品文,並非是全然相異的兩種文體,而更近於光譜的不同面向,有其相似處,更可以互相觀察。正近似於此,劇情片與紀錄片與其說是全然不同的影像,不如說或多或少具有真實性。
形式與內容的繫連
「我覺得要提防的是,不能要把什麼都說成是風格與形式。」羅福林老師分享近年研究影像的心得,提及自身對於跨學科資料、老年研究的涉獵與參考,背後的動機是為了避免只是停留於抽象的形式層次,為審美而審美。一旦捨棄具體的老年議題,研究影像中的老人形象就會抽離出具體脈絡,而使得老人形象只是被影像研究消費的符號。
美感、風格及形式研究不僅不能和現實脈絡區分,也不應該和文本內容切分。形式和內容,並非二元對立,形式往往即是內容。從電影而言,就有導演會刻意使用類似紀錄片的形式,藉以帶來真實感。當然,這不是意味劇情片與紀錄片沒有差異,劇情片通過導演的控制、加工及劇本,是通過規劃的製造品,然而紀錄片沒有劇本,畫面也較為紛雜,訊息以相較混雜的方式呈現。部分獨立紀錄片導演,甚至有意追求訊息的不可預測性,並將之視為紀錄片的神髓。
如果以旁白而言,在商業或政治宣傳的紀錄片中,總是存在著強而有力的旁白,它的聲音是真理的所在,它四處存在,但是觀眾卻無法辨認聲音從何而來,為何能掌握權威。相較於此,獨立、具批判性的導演則試圖顛覆旁白。在《跳舞時代》中,旁白只是在必要的時候提供背景,介紹被採訪的人等,而影片的聲道更多是讓人物自己發聲,在聲音的混亂中,反而讓諸多主題自己呈現,由於沒有明確的主軸與引導,反而啟發觀者對於許多議題的思考。再以兩個紀錄片為對比,柴靜的《穹頂之下》討論汙染問題,偏向以旁白的聲音為中心主導,但是王久良的《垃圾圍城》講北京非法垃圾場,電影僅呈現問題的後果,卻未告訴觀影者任何解答,而只是引導觀者從影像進行反思。
談到關於一些紀錄片被批評具有感傷傾向的批評,羅福林教授認為像是《跳舞時代》就並不感傷。它固然以相當讓人舒服、讓人享受娛樂的方式,似乎只是敘述對過往充滿懷舊的故事、紀錄收藏唱片的生活樂趣等等。但是,若從政治宣傳的角度,身在殖民時期的生活,不是應該描寫黑暗、痛苦的經驗嗎?但是《跳舞時代》顯然沒有這麼做。這事實上意味著歷史經驗並不如政治宣傳一樣單一,因而也是呈現政治鋒芒的巧妙方式。古倫美亞唱片公司顯然是出於商業目的,卻也無意間培養了本土文化,因而形成台灣認同的基礎。因此電影實際上並未將問題從政治角度予以簡化,反而是呈現現向的複雜化,此中呈現的不僅是藝術價值,也同時是人文價值。
老年與遺像
在幾次演講中,羅福林教授都提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以降對於青年的推崇,並反思:與年輕的範式相對,是否也存在老的範式?不過,羅福林教授進一步說明:具體而言,這當然不是意味著五四時期或當代文化可能存在對老人的推崇。以老年人在影像中的意義而言,羅福林教授認為老年意象是批判主流商業影像的方式,是跳脫出主流審美,而提醒在消費文化之外存在的生活真實性。
老人固然不取代青年,從另一個面向而言,今日的老年人正是昨日的革命青年,特別是經歷過革命後果,成為對革命抱有遺憾的老人,自身即是歷史的化身,呈現歷史變遷,但這當然也是具有特殊時代脈絡的現象,二三十年後的老年人,也已經不曾經歷革命了。
羅福林教授對於電影中的老年研究,切入點之一是遺像。他指出,在大陸電影中目前已經蒐集到許多文本案例。遺像不一定是相片,也可能包含遺物。遺像弔詭的意義在於它見證人存在的時間,但是遺像的呈現意味著人已死去。正如同照片捕捉已失去的時間,同時是在與不在。遺像或許某程度即是紀錄片的象徵,或者說紀錄片即是遺像。
回到老年意象,如果說老年是批判主流商業的方式,老年或許意味著障礙者,因此更大的範疇是主流價值中被邊緣化的人群,因此大陸許多紀錄片拍攝了精神病患、毒癮等邊緣者的畫面。老年研究,某程度而言是羅福林教授研究邊緣影像的一個切入點。
給年輕學者的建議
「我年輕時美國的學術訓練,好像就是習慣批判主要影響的學者著作,作為研究的基礎,我覺得這個不太好,好像是以前的研究沒有價值」比起耽溺於否定前人,刻意求奇求變,羅福林教授建議研究應該以合作、不同學者跨領域協力研究為方向,會比起一味排詆前人更有意義。
對於當今學習中國文化的年輕學子而言,越來越嚴峻的問題是漢學是否還被視為是一種專業對待。專業意味著有他自己學科的研究方法,像是人類學有其方法、歷史學有其方法,然而近年美國學科的配置漸漸傾向跨學科或者跨專業發展。
漢學家的培訓的前景,在美國面臨嚴峻挑戰。許多大學不再設立具體語種、文化或區域的研究學門,像是德語文學系、義大利、葡萄牙……都越來越少。空疏不紮實的全球學在美國非常流行,而至於紮實鑽研的區域研究,現在集中在最古老的常春藤大學,才保有嚴實的亞洲學的研究,具有區域研究的研究資源與能力。如果照現在美國高教發展,漢學訓練或許會逐漸消失,做中國文化研究的可能只剩下母語中文的研究者,使人遺憾。
羅福林教授建議青年學子,應該要看世界各地有哪些地方可以紮實培訓中國文化,因為有這樣條件的教研單位,在美國越來越少。近年香港大學中的發展傾向特別有意義,因為除了華人,也有很多歐美研究者在香港做中國研究,因此呈現多元的樣態。
採訪撰稿:吳佳鴻(台大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