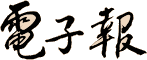聲音、溫度與人間:陳培豐教授專訪
學人動態
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電子報第17期
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電子報第17期
2014-03-10

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的陳培豐教授,甫獲得102年度國科會的「傑出研究獎」。求學過程相對迂迴的他,對於學術研究,實有與其他學者不同的深刻體會。跨領域的研究相對具有難度,如何在漫無邊際的資料汪洋中拼湊、分析出問題的答案與詮釋的輪廓?但陳培豐教授認為,那正是趣味所在。研究不只是資料的搜索與堆砌,更需要對問題的敏感、對人間的關注,那所成就的,正是一種具有溫度的學術高度。

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的陳培豐教授,甫獲得102年度國科會的「傑出研究獎」,他的兩本專書《「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想像與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前者就「同化」的觀點切入,看出日本殖民臺灣時期「同化」政策與其他殖民國家的差異性,更細緻地描繪臺灣殖民地時期的精神面貌;後者則透過日治時期「漢文」的混成現象,切入背後隱含的政治、文化、社會、階級、思想與歷史意義。兩本著作皆是日治時期臺灣語言、思想、認同相關研究領域的重要論著,但與其他學者一路求學、任教的順遂經歷有些不同,陳培豐教授在正式踏入學術圈之前,經歷了相對更為迂迴的路程,回國之後也在不同的研究環境中轉換。「我很多事情都經歷了兩次,例如五專加上日本的大學生活等於讀了兩次,碩、博士入學考了兩次,碩博士論文也寫了兩本,回國之後升等也都經歷了兩次……」這些重複不見得是繞道與浪費,在這樣反覆地試驗、重來之中,無形中立穩了根基,也對許多課題有了更多重、深刻的體會。
陳培豐教授在成長過程中有許多與語言、聲音密切相關的經歷,在《「同化」的同床異夢》以及《想像的界限》兩書的後記裡,不難看到個人生命中,「國語」、「母語」、「外語」不斷交錯、衝突的體驗,這些埋伏在記憶中的疑問,卻透過嚴謹的學術語言層層地鋪展開來。
「在做歌謠研究之前,其實我的童年就充滿了這種關於唱片、音樂、聲音的記憶,當然也跟我曾經待過唱片業界的經驗有關。總之我覺得人生的境遇很奇妙,冥冥之中好像有某種關連。特別是走上學術之路,對我而言純屬意外。但我認為不管你選擇走上學術之路的動機純不純、高尚不高尚,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後你必須為你的選擇以及人生負責。」
《想像的界限》一書當中,談的是臺灣語言、文體的混成現象,這些文體的混成不只是文人、知識分子的書寫的問題,同時也是庶民生活的語言現象。從日治時期的報刊文章到聽歌識字的歌仔冊,從知識分子的漢文到卡拉OK的字幕,從臺灣話文到「宅女小紅」的文體混生……「所以我覺得歌謠研究很有意思,那裡面其實有很多我們過去忽略的、不常注意卻極為重要的環節。」那混合與再生的,不只是臺灣歷史中語言與思想的軌跡,似乎也是陳培豐教授自身經驗的寫照,稍晚起步的學術路程,反而讓他在迂迴繞道的過程中,觀察到更多關於語言、聲音、認同的圖景與線索,不同學科的混合、再生與碰撞,也帶來了更為不受限的學術視野。「而這些都不是四十歳之前的我可以融會通貫快速理解並加以運用的。以結論來說,晚起步對於我來說,其意義是在研究sense的累積,是資産不是負債」。學術寫作正如同其他媒材的創作,需要溫度,需要社會關懷,需要對人情、世態的感覺與敏感,陳培豐教授的自我思考與學術實踐,正是最佳的寫照。

撰稿:馬翊航(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的陳培豐教授,甫獲得102年度國科會的「傑出研究獎」,他的兩本專書《「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想像與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前者就「同化」的觀點切入,看出日本殖民臺灣時期「同化」政策與其他殖民國家的差異性,更細緻地描繪臺灣殖民地時期的精神面貌;後者則透過日治時期「漢文」的混成現象,切入背後隱含的政治、文化、社會、階級、思想與歷史意義。兩本著作皆是日治時期臺灣語言、思想、認同相關研究領域的重要論著,但與其他學者一路求學、任教的順遂經歷有些不同,陳培豐教授在正式踏入學術圈之前,經歷了相對更為迂迴的路程,回國之後也在不同的研究環境中轉換。「我很多事情都經歷了兩次,例如五專加上日本的大學生活等於讀了兩次,碩、博士入學考了兩次,碩博士論文也寫了兩本,回國之後升等也都經歷了兩次……」這些重複不見得是繞道與浪費,在這樣反覆地試驗、重來之中,無形中立穩了根基,也對許多課題有了更多重、深刻的體會。
他談起一開始的留學生活,當初並未設想之後會走上學術之途。在留學生階段担任全早稻田大學和臺灣留學生雜誌的總編輯,頓時成為了風雲人物。「大家都認為我應該是很博學、讀很多書,但當其他人來到我的住處的時候,都非常的失望,書架上並沒有幾本書。當我在踏入學術圈之前,我其實是一片空白的。依靠的是自己的社會經驗而非知識累積。」空白,卻也代表著不被當時既存的一些思考框架或黨國知識體系所左右,有更多自己去想問題或問問題的契機。在陳培豐教授的著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清晰的問題意識與挑戰,例如《「同化」的同床異夢》,質疑了過往討論日本殖民臺灣時近代化中「光明面」與「黑暗面」的對立,『想像與界限』則破除了過去將「漢文」「日語」互相對立的研究框架。「這些啟發與訓練,真的還是要感謝我在東大的老師,若林正丈先生。他讓我從一個原本存在於距離學問最遥遠之一端的門外漢,在短期間變成了一個上得了檯面的研究者。」
於東京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陳培豐教授,認為自己在學術議題辨識的敏銳度與整合能力,多來自於當初在「總合文化研究科」之下的學術訓練。總合文化研究科是戰後東京大學內新興學科,跨領域研究的重鎮。「四十歳才進入博士班的我不像其他學者一樣,是文學研究、歷史研究的科班出身。因此,在學術上我沒有那麼豐碩的積累與背景可做依靠,我没有平坦大道可走,而必須像走鋼索般的小心謹慎、且精確的去尋找學術上的新問題以及方法,並引導出有效的詮釋框架、有趣的見解或答案」。而除了社會經驗所萌生出來的直覺之外,這些「走鋼索」的能力,都是在跨領域研究訓練中磨練出來的。「這是我的缺點,但也同樣是我的優點。就像臺灣文學,它的優勢不在於文本的『數量』,而是隱藏其中的問題性。所有的研究,問題意識和方法都是最重要的。」做研究時問題意識、方法有時候是比知識重要的。重視後者忽略前者,似乎是臺灣學界的傾向。
透過跨學科的方式,能夠解決過去單一學科所無法解決的複雜問題。發現問題其實並不難,如何在漫無邊際的資料汪洋中拼湊、分析出問題的答案與詮釋的輪廓,才是最難的部分。當文學、特別是漢詩文研究不再只是文本賞析的時候,研究者所要處理的問題就更加的複雜,陳培豐教授認為,那正是趣味所在。
「那其實要憑著某種直覺,某種sense。我很喜歡觀察人,我在日本出差的時候喜歡住在上野、淺草等有歷史、以及複雜人際關連的老社區,可以看到很多東西。而我自己成長的艋舺就是類似這種地方。」
研究直覺來自於對人與世間百態的觀察與體會。陳培豐教授在日本留學期間曾經以短篇小說〈歐多桑的時代〉獲得第十四屆的時報文學獎,同年得獎的還有駱以軍的〈手槍王〉。〈歐多桑的時代〉描寫了敘事者受日本教育的父親,戰後經歷了歷史、語言的雙重斷裂,而小說中童年時期不被父親疼愛的「我」,卻因為寫作上的表現,隱隱彌補了親子、歷史之間的裂痕與創傷,微妙地展開了臺灣戰後不同世代間語言、政治認同、親情、記憶與歷史間微妙的接合與分裂。「這篇小說中的主要成分都是虛構的,但這些和失語的一代有關的虛構確實延伸自我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思考,而不是課堂上的歴史知識。也或許因此才有說服力、生命力」。對他來說,歴史的可能性不僅存在於資料文獻,也可用推測想像去獲取印証。而既然准許複數答案的存在,那麼人文科學研究其實也是一種創作。只不過這種創作要有「科學」根據、且禁得起「客觀理性」的檢驗。「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不是嗎?所以只要你做得好、做得適當,它必然會回歸到當下的臺灣――一個具有某種主體性的臺灣。所以不要過度被「愛臺灣(或中國)」的使命感給「綁架」,就放手去做、大膽去做,讓不預設立場的知識好奇心引導著你去做,反而能做出有温度有說服力的研究。我覺得最近KANO的導演馬志翔有一句話說得很好——歷史是有情感的,他想拍出的電影,是要有人的溫度。我覺得好的研究也是這樣,是不能跟人的經驗分裂的。」
透過跨學科的方式,能夠解決過去單一學科所無法解決的複雜問題。發現問題其實並不難,如何在漫無邊際的資料汪洋中拼湊、分析出問題的答案與詮釋的輪廓,才是最難的部分。當文學、特別是漢詩文研究不再只是文本賞析的時候,研究者所要處理的問題就更加的複雜,陳培豐教授認為,那正是趣味所在。
「那其實要憑著某種直覺,某種sense。我很喜歡觀察人,我在日本出差的時候喜歡住在上野、淺草等有歷史、以及複雜人際關連的老社區,可以看到很多東西。而我自己成長的艋舺就是類似這種地方。」
研究直覺來自於對人與世間百態的觀察與體會。陳培豐教授在日本留學期間曾經以短篇小說〈歐多桑的時代〉獲得第十四屆的時報文學獎,同年得獎的還有駱以軍的〈手槍王〉。〈歐多桑的時代〉描寫了敘事者受日本教育的父親,戰後經歷了歷史、語言的雙重斷裂,而小說中童年時期不被父親疼愛的「我」,卻因為寫作上的表現,隱隱彌補了親子、歷史之間的裂痕與創傷,微妙地展開了臺灣戰後不同世代間語言、政治認同、親情、記憶與歷史間微妙的接合與分裂。「這篇小說中的主要成分都是虛構的,但這些和失語的一代有關的虛構確實延伸自我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思考,而不是課堂上的歴史知識。也或許因此才有說服力、生命力」。對他來說,歴史的可能性不僅存在於資料文獻,也可用推測想像去獲取印証。而既然准許複數答案的存在,那麼人文科學研究其實也是一種創作。只不過這種創作要有「科學」根據、且禁得起「客觀理性」的檢驗。「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不是嗎?所以只要你做得好、做得適當,它必然會回歸到當下的臺灣――一個具有某種主體性的臺灣。所以不要過度被「愛臺灣(或中國)」的使命感給「綁架」,就放手去做、大膽去做,讓不預設立場的知識好奇心引導著你去做,反而能做出有温度有說服力的研究。我覺得最近KANO的導演馬志翔有一句話說得很好——歷史是有情感的,他想拍出的電影,是要有人的溫度。我覺得好的研究也是這樣,是不能跟人的經驗分裂的。」
陳培豐教授在成長過程中有許多與語言、聲音密切相關的經歷,在《「同化」的同床異夢》以及《想像的界限》兩書的後記裡,不難看到個人生命中,「國語」、「母語」、「外語」不斷交錯、衝突的體驗,這些埋伏在記憶中的疑問,卻透過嚴謹的學術語言層層地鋪展開來。
「在做歌謠研究之前,其實我的童年就充滿了這種關於唱片、音樂、聲音的記憶,當然也跟我曾經待過唱片業界的經驗有關。總之我覺得人生的境遇很奇妙,冥冥之中好像有某種關連。特別是走上學術之路,對我而言純屬意外。但我認為不管你選擇走上學術之路的動機純不純、高尚不高尚,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後你必須為你的選擇以及人生負責。」
《想像的界限》一書當中,談的是臺灣語言、文體的混成現象,這些文體的混成不只是文人、知識分子的書寫的問題,同時也是庶民生活的語言現象。從日治時期的報刊文章到聽歌識字的歌仔冊,從知識分子的漢文到卡拉OK的字幕,從臺灣話文到「宅女小紅」的文體混生……「所以我覺得歌謠研究很有意思,那裡面其實有很多我們過去忽略的、不常注意卻極為重要的環節。」那混合與再生的,不只是臺灣歷史中語言與思想的軌跡,似乎也是陳培豐教授自身經驗的寫照,稍晚起步的學術路程,反而讓他在迂迴繞道的過程中,觀察到更多關於語言、聲音、認同的圖景與線索,不同學科的混合、再生與碰撞,也帶來了更為不受限的學術視野。「而這些都不是四十歳之前的我可以融會通貫快速理解並加以運用的。以結論來說,晚起步對於我來說,其意義是在研究sense的累積,是資産不是負債」。學術寫作正如同其他媒材的創作,需要溫度,需要社會關懷,需要對人情、世態的感覺與敏感,陳培豐教授的自我思考與學術實踐,正是最佳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