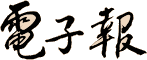在島嶼,築起搭蘆灣:專訪孫大川教授
學人動態
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電子報第23期
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電子報第23期
2014-09-11

十數年來,孫大川教授長期關注原住民傳統文獻的整理、蒐集與撰述,他常以「述而不作」,來形容自身的學術理想。目前擔任監察院副院長的他,對於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差異,卻有著他自身圓融務實的理解與詮釋。孫大川教授理想中的知識分子與文化藍圖,有著彈性十足,亦務實亦豪俠的面向。透過訪問孫大川教授,我們可以想像一種姿態,不必然是「搖擺」於學術與政治,理論與實踐之間,而是兼容共存,彼此證成的。
 撰稿:馬翊航(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撰稿:馬翊航(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政治與學術,實踐與機緣

政治與學術,實踐與機緣
孫大川教授在著作《搭蘆灣手記》中曾說「俠儒之間,原本不必然是相衝突的,關鍵就在我們能不能隨遇而安,保持生命的流暢,走到哪裡就成就到哪裡……。」(孫大川,〈文獻作為一種志業〉)。那是2003年初,當時他已卸下原民會副主委的職務,進入東華大學民族語言學系任教。十數年來,他積極地投入臺灣原住民語言與文獻的整理,包括編選《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輯》、《臺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成立原住民族文獻委員會,並持續推動臺灣原住民文學的日譯、口傳與祭儀文學的蒐集與整理。他常以「述而不作」,來形容自身的學術理想。「與原住民文化相關的資料,有太多需要整理,更需要對各族文化、語言有一定理解的人,來協助整理與記錄。這些年來,我們所推動的計畫與研究,也許有了某些成果,但那只是個開端。」由於數位典藏技術的逐漸成熟,讓原住民的相關文獻工作變得相對便利,但在龐大的資料之下,其實更需要的是能夠適當詮釋、篩選文獻資料的人才。孫大川教授以卑南族南王部落與知本部落的名稱為例,說明即使族人本身,也會在不明瞭部落歷史與語彙本義的狀況下,作出錯誤的詮釋。如何避免口耳相傳中的訛誤,如何辨認文字與口述材料是否經過後人的再創作、發明……這些工作都非一朝一夕能夠完成,更需要能夠忍耐文獻工作之枯燥寂寞的研究人才。
而孫大川教授日前第三次入閣,榮任監察院副院長。十年光陰過去,我們好奇,他從學界重回政壇,心境上有什麼樣的轉變? 對於原住民的文化事務與發展,是否有不同的期待與想像?
「其實這個過程沒有太多的猶豫。也許是性情使然,對我來說,學術研究與政治服務,對我來說都是一種實踐,一種機緣。」
孫大川教授談起,他最近開始重讀明清以降的士人文章,明顯感受到一種鬱結、難以施展的苦悶。在政治現實與個人追求間的矛盾與不滿,往往讓他們的作品裡面,失去了某種承擔的性格。他反而在中國西方傳教士留下來的文獻中,接觸到了更貼近底層、庶民生活的某種眼光。「我認為知識分子不必然只是停留在知識的小圈圈裡面,而是可以具備俠氣,豪氣,更開闊,更具有行動力的。例如劉鶚筆下的老殘,就是某種典型。」在學院中,他對於原住民政治事務與文化議題同樣關心;擔任政務官時,卻仍舊心繫原住民文獻與文化保存,以及原住民文學翻譯、推廣等議題。除了自我學術實踐的期待,他也提到天主教信仰中的入世精神,以及務實的性格特質,都讓他在不同位置的變動中,找到一種圓融而彼此貫通的姿態。
To Have 到 To Be──原住民文化的挑戰與轉機
孫大川教授曾以「黃金十年」來形容90年代原住民在公共事務、文化藝術上的主體建立與進展。立足2014年的當下,再回首過去十年,相較於先前的黃金時代,原住民的文學與文化研究,以及公共事務上,如何延續此前的氣象?是否有著不同的挑戰與轉機?
「我常常認為過去我們原住民面臨的是一個 『to have』的問題,我們在90年代尋求種種資源與協助,希望在各個領域被看見。但在現在,我們自己所要面對的,更是一個『to be』的問題。」「to be」是一種主體尋求的過程,如果原住民族群從「to have」的階段取得了文化發展上的進展,下一階段,要如何擺脫對種種外部資源的依賴,重新回復原住民各族群內部的文化完整性,更是一個值得思索的課題。
「當我們積極地尋求公部門的資源,舉行祭儀、文化活動的時候,是否遺忘了,當我們從前沒有國家、沒有補助的時候,祭典同樣在進行啊。」如何從國家「治理」與選舉事務的資源分配綁架中逸脫,恢復自身文化中有機、循環的生命觀、宇宙觀,也許是他更為在意的面向。這並不代表原住民族群不需要為資源分配的不公、相關權益的追求而抗爭,「我認為我們在資源與權力的誘惑以外,更需要反觀族群自身的弱點與侷限。例如我也認為,原住民的研究者、寫作者,不必僅止於觀看族群內部,更應該走出去,與其他族群對話與接觸。就像我的寫作,更多時候是面向漢人讀者的。」
原住民書寫與研究的新視野
尋回主體,不必然是封閉與依賴,更可以是拓展與對話。「之前我們一直在推動臺灣原住民文學的外譯,在日文方面已經有了很好的成果。日本的翻譯者,經由翻譯臺灣的原住民文學,對臺灣的原住民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有些更與臺灣的原住民作家成為了知交好友。」而日後由於臺紐經濟合作協定的簽訂,開啟了雙方許多文化交流的機會,紐西蘭原住民與臺灣原住民同屬南島語族,在語言文化、歷史經驗上,存在許多對話與互動的可能。明年臺北國際書展的主題國為紐西蘭,也將安排臺紐雙方作家、出版社的交流,將為臺灣的原住民文學書寫、出版、研究,帶來許多刺激與想像。「我甚至想過,何不在臺灣的原住民部落中,設置一個『作家之屋』?提供國內、甚至國際的寫作者,一個與部落文化接觸的寫作空間,部落的生命經驗,自然地就會滲入他們的寫作當中。」孫大川教授也高度肯定近十年來原住民寫作者的成績,像是巴代陸續創作的長篇小說,瓦歷斯‧諾幹在書寫題材上的開創,乃至於原住民族文學獎所帶出的新一代創作者,「我想在創作上,我們是沒有交白卷的。」
這幾年臺灣的新生代原住民相關研究者,在孫大川教授的觀察下,在研究趨勢上,是否有什麼樣的變遷與進展?他認為,無論是在題材的選定或視角的開展上,的確有一些年輕的研究者,找到了嶄新的路徑,但令人驚喜的研究並沒有預期的多。「這當然不只是研究者的問題,也許與研究材料拓展的速度不夠快、不夠多也有關。也許這幾年新的創作、或者新的文獻的整理,會刺激一些年輕研究者的想法,應該還是值得期待的。」然而在主題與論點之外,他更期待的學術語言是,有身體感、有生命經驗,能夠體貼常民生活文化脈動的研究。「我認為部落中人物的傳記、口述歷史的紀錄與整理,同樣也是非常重要的工程。」在文獻、歷史記憶中,其實蘊藏著無限細微複雜的生命經驗,歷史的內部同樣仍藏有許多,值得以部落觀點重述、翻轉的事件。這些尚未被照亮、點明的經驗與記憶,仍然等待新一代的研究者燃起火種。
在島嶼,築起搭蘆灣
提起下一個階段的學術寫作,孫老師有著嶄新的想像。「我覺得現在的臺灣文學研究題材,似乎都很『痛苦』,我想,臺灣文學應該也有『喜樂』的那面吧,我希望能把這個面向書寫出來,也同時檢視臺灣文學研究、原住民文學研究當中的一些問題。」實踐與愉悅,在地與世界,孫大川教授理想中的知識分子與文化藍圖,有著彈性十足,亦務實亦豪俠的面向。我們可以想像一種姿態,不必然是「搖擺」於學術與政治,理論與實踐之間,而是兼容共存,彼此證成的。
那讓我想起他的〈搭蘆灣〉一文所說的:
「搭蘆灣(taLu’an),阿美語,指山上或田間的工寮,是我童年最鮮明的記憶之一,也是我對『家』延伸的第二種理解……搭蘆灣其實是我們鋼筋水泥的家和我們自然屬性的窩之間柔軟的建築形式,它提醒我們在工業、科技的威勢中,如何安立一個可以和大自然對話的家。」
孫老師監察院的辦公室中,雅致地擺放著來自部落的織品、雕刻作品,這些帶著經驗與情感的物件,軟化了剛硬的行政空間,與孫老師一同呼吸著搭蘆灣的嚮往與想像。那裡面有著人的勞動與生命的節奏,是有彈性的文化記憶,溫和而堅毅的姿態。知識與實踐之間或許不矛盾也不擺盪,因為所在之處,即是他的搭蘆灣。
(圖片提供:山海雜誌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