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0年3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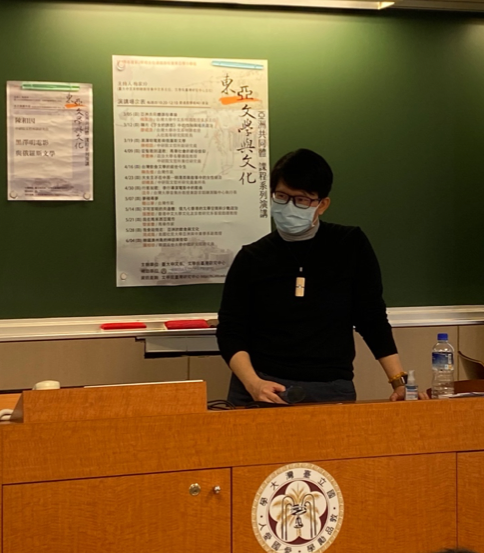
本週講座,邀請到中研院文哲所副研究員陳相因,陳老師長期耕耘俄國文學研究,研究成果豐碩。這回來與同學分享俄羅斯文學與黑澤明電影的神秘關係。陳相因指出,黑澤明大約有五分之一的電影直接改編了俄羅斯文學,如《白痴》、《生之欲》、《在底層》、《得蘇・烏札拉》,此中臺灣讀者較熟悉的作者為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等。陳相因以「文化差異(Culture difference)」作為研究方式,以此分析也能使華語觀眾有更多想法。
黑澤明在1928年加入了無產階級美術研究所,導致他一生都受到日本特務監視著。他最初想投入「寫實主義」的懷抱,因此透過閱讀俄羅斯文學。「寫實主義」能夠讓他表現他所看到的,不願粉飾生活的真相。黑澤明非常關注社會,他認為閱讀杜斯妥也夫司基的作品有助於看見人內心的深度。《白痴》是一本四部曲小說,黑澤明改編成電影,共拍了四個小時。陳相因比較了原作與黑澤明改編電影的差異。原作中,杜斯妥也夫司基寫主角看到美女「第一眼的印象」,以及第二次「凝望照片」的驚嘆感受,到最終忽然感受「美的降臨」。黑澤明選擇用不同的電影手法還原,在改編版本中,我們很難看到杜氏文字中的咄咄逼人,因為黑澤明相信「美」可以拯救世界。然而,日本觀眾的反應不如預期,原因可能在於「白痴」一詞在日本語境中少用,使得觀眾一頭霧水,此中顯示出日俄文化差異。且俄國讀者熱愛議論、探討哲學問題,也使的作品與日本觀眾有隔閡。黑澤明也改編托爾斯泰,將小說《克里》轉化為電影《生之欲》。他將日本社會語境與這本中篇小說融入得很好。他看到了「官僚」生活與體制的問題,感受到官僚與民眾關係之間強烈的阻隔,以及所產生的弊端。他採用「眾聲喧嘩」的技法,以聲音的喧鬧表示多種意志的衝突。黑澤明也修改了托爾斯泰的「說教」口吻,黑澤明將《生之欲》譯為「活下去」,討論「何謂活得有意義」,與托爾斯泰強調「人要幫助他人才有意義」不同,黑澤明避免了這種說法,更有利於日本觀眾的接受。
陳相因認為,黑澤明改拍得最好的俄羅斯作品是《底層》,此作改編自高爾基小說。這些經驗來自黑澤明童年經歷,可參考他的自傳《蛤蟆的油》。此時日本大肆搜索共產黨員,黑澤明因而飢寒交迫,流落在底層,因而深有所感。在蘇聯時期,「階級」看似被消滅,但其實仍存在(從穿著即可看出)。黑澤明的這部改編,以低成本短期的拍攝,呈現出比法、俄、中等國家的改編版本更好,不僅尊重原著,也具世界主義的先鋒性、藝術性,並成功地融合在地化。且能真正告訴觀眾,社會底層真正的生活為何?從黑澤明的童年經歷來看,部做品也反映出日本江戶時期底層生活的活潑,有賭錢、飲酒等樂趣。黑澤明意圖表達底層中有一種「原始的歡愉」,融入了日本文化,因而帶來反差的效果。後來的黑澤明,因票房低落而萬念俱灰,他無法向銀行貸款。他在1971年自殺獲救。在《底層》這部作品高度的成功之後,卻無以為繼。此一現象也與「彩色電影」的出現有關,於是,他接受蘇聯的資金拍攝阿爾謝尼耶夫的作品。蘇聯看重他長期批判日本社會的動力,試圖接軌國際與他合作。阿爾謝尼耶夫作品的場景在西伯利亞,在一個有多種文化的地區,如何保存、碰撞是重要之事。黑澤明改編了阿爾謝尼耶夫的作品《德蘇烏札拉》展現了東方的觀點。原著中描寫西伯利亞的中國人、赫哲人、朝鮮人、日本人、俄國人等多民族,其中對中國人多有批評,不乏俄羅斯的主觀心態。但是在黑澤明的改編中,他讓此地變成一個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場地,有助於我們了解西伯利亞這個地區,恐怕不是和諧無衝突的。
陳相因最後鼓勵同學,不用怕犯錯,可以多學習不同語言,去看不同文化的東西。正如同《白痴》裡所說,他對於祖國有很多不切實際的理想,卻令人喜愛。因為他年輕,因此承受得起錯誤。大家要多去看看世界,再回來審視自己的文化。梅老師認為,陳相因老師的講授給同學好多把鑰匙,有助大家去了解黑澤明電影的大門。從文學作品到電影語言、美學與詮釋,產生了不同的效果。聆聽演講後收穫頗豐,也提醒了過去我們少有意識到的階層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