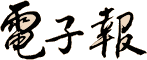抒情與本土的相遇——專訪青年學者鍾秩維
學人動態
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電子報第69期
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電子報第69期
2020-12-29

鍾秩維,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畢業,並於同校的臺灣文學研究所獲得碩、博士學位。曾任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Hou Family Fellow,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培育人員。現職臺大文學院「趨勢人文與科技講座」博士後研究員。研究興趣包括臺灣文學、抒情傳統與當代批判理論,著有博士論文《抒情與本土:戰後臺灣文學的自我、共同體和世界圖像》(2020)。
廣博的學思發展 從政治系到臺文所
今年(2020)甫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的鍾秩維,博士論文《抒情與本土:戰後臺灣文學的自我、共同體和世界圖像》同時獲得臺灣中文學會「四賢博士論文獎」與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文學傑出博碩士論文獎」青睞,備受肯定。
在這本論文中,他以「抒情與本土的相遇時刻」為思考起點,聚焦戰後臺灣文學,考察個案包括王禎和、白先勇、朱天文、李喬、李渝、宋澤萊、邱妙津、楊牧、夏宇、舞鶴、齊邦媛與鄭清文這些分佈於差異的世代、政治意識形態、文學場域習癖、美學流派,乃至性別與性取向光譜上的作家至於文類方面,除了慣見的小說、詩和散文之外,亦處理回憶錄、文學(史)文論、乃至藝術(繪畫、電影等)批評等等的材料,期待藉此能夠對流行於戰後文學場域中的「抒情」和「本土」論述,有全面性的觀察。在方法學上,鍾秩維試圖以跨領域的角度來釐清在「臺灣文學本土論」與「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之交錯和交鋒中,所暗示的華語語系文化如何受容、轉化「中國性」的問題。
現職臺大「趨勢人文與科技講座」博士後的鍾秩維,曾以「侯氏訪問學人」(Hou Family Fellow)的身份赴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交換一年,學術經歷豐富。觀察臺、美學風的相異之處,他發現哈佛學生比較勇於爭取機會、表達想法,在撰寫論文時,除了指導教授,也與committee的成員保持更密切的聯絡,便於在即時的討論中補充、乃至修正論點。同時,「在美讀書的學生似乎也較樂於互相切磋學術觀點,甚至分享材料,我滿欣賞這點,所謂『獨學而無友則孤陋寡聞』,做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對話對象』。」這也與鍾秩維追求深廣的學術取向十分契合。在研究生階段,除了跨系跨領域選修,複雜化自己的學術視野外,他也規律地與跨系所的成員一同舉辦讀書會,主題通常是新興的學術議題,包括視覺文化、華語語系與漢文脈;也會對經典的思想家做精讀,例如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柄谷行人等。他認為讀書會很能激盪不同的觀點,從而多面向地開拓新的研究取徑。
進入臺文所之前,鍾秩維就讀於臺大政治系,系上學風自由,當時他已廣泛接觸社會系、外文系、中文系與歷史系的課程,這些經驗都成為他往後在臺文所展開思辨的基石。研究所期間,恰逢李渝、史書美、白先勇和王德威等海外知名作家、學者,先後應「白先勇文學講座」之邀,在臺文所擔任客座教授。其中李渝、白先勇以及負責該講座的柯慶明教授,均為臺灣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的直接的參與者,鍾秩維碩一時修習李渝「文學與繪畫」、「小說閱讀和書寫」課程,接下來也長期擔任白先勇與柯慶明大學部課程的助教,耳濡目染下,對於那一世代人的文學觀,以至於看待世界的方式特別親切,臺灣現代派遂也成為他博士論文實例主要的取樣對象。
質疑與拓寬 「喚起」世界中的抒情
「抒情」與「本土」,此二看似矛盾的現象,其實具有值得透過比較,來進一步深省之處,就如鍾秩維說起發表於今夏的博論時指出:「我將抒情和本土兩個問題並置,前者上接學者對於中國文學與文化的本質為何的界定,後者是臺灣文學批評家追尋本土國家意識的意圖,它們看似背道而馳的兩種民族主義慾望。」不過,他也指出,追究「抒情」與「本土」論述在戰後臺灣興起的時間,會發現它們都與七、八〇年代一系列內政、外交的壓力息息相關,某種意義上,它們都反映了島民對於什麼是「臺灣人」的身份/認同(identity)焦慮。「本土」作為一種定義臺灣人身份的話語自不待言,鍾秩維進一步提及,「抒情傳統」也是在地對於「中國」文學具有創意的轉化,或可視為臺灣對於中國文學的一種「批判性的繼承」。
循此,面對有關「抒情傳統」不夠「本土」的批評聲音,鍾秩維如此回應:「『抒情傳統』本質上是一個『現代的發明』,它的出發點是『海外』的華人離散社群,而尤其立足於『台灣』。在這個意義上,『抒情傳統』的『現代性』問題,不免也就是『中國古典文化』如何在中國大陸之外的區域,重新被詮釋、被發明的問題,而這個過程透露的,毋寧是某種『花果飄零,靈根自植』的期待。」用當代理論的話來說,他認為這種將關注的焦點會從「中國」本身,移到「非中國」的地方如何接受、新創「中國(性)」的轉向,正標誌出了「華語語系」(Sinophone)研究的起點。
沿著這一問題來說,對於「抒情傳統」以今律古,透過西方來看中國的質疑,鍾秩維首先回顧晚近學界如何回應「何謂中國」的質疑。如許倬雲、葛兆光等學者都已經提出,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中,「中國」何所指的內涵一直處於變動,尤其以「漢字漢文」為基礎發展生成的「中國」文化,古往今來都在「文」與「言」界限的建構和解構之間,反覆釐定何為「他者」,而表述「自我」為何。換言之,「華」「夷」之間不見得壁壘分明,從我們今天的後見之明看來,也未必有孰高孰低的階序。在這個意義上,「抒情傳統」不過是前述歷史長流此時此刻的一種演繹,相對之下,民族主義者排他性的、本質主義式的「中國」定義,反而才真正是以今律古的說法。鍾秩維提到,近來王德威教授借用史學家杜贊奇(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的說法,呼籲 “Rescuing Literature from the Nation”,而認為誠哉斯言。
將話題帶回臺灣,鍾秩維說:「有語言學的研究指出,『臺灣』一名來自西拉雅話中的“Tai-an”或“Tayan”,指『外來者』,從此可見,不只何謂『中國』,就連何謂『臺灣』,答案都指向本土與外來元素不斷協商的動態過程。但這並不等同於我們可以就此逃離民族主義,它畢竟主導了現代以來人類最主要的共同體論述;而是作為人文研究者,我們仍要與它保持一個讓批判得以展開的距離。」這一必要的距離,使鍾秩維跳脫民族主義的框限,對「抒情」與「本土」進行比較研究;此外,此一距離所給予的啟示也能從他在「2020臺灣理論關鍵詞」會議上提出的「笑詼(tshiò-khue)」看出端倪。該研究雖然立基臺灣文學獨特的語體,嘗試鉤沉臺灣人喜感現象的理論暗示,但在理論化的過程中,亦不可能繞過中國與西方對「笑」的理解。畢竟臺灣的語文狀況,一直都在跨文化的流動中混生。
同理,在鍾秩維的臺灣文學研究進程中,除了中文抒情傳統,西方文學與文化理論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參照意義。他注意到在近來有關lyricism和詩歌的理論辯難中,逐漸發展出一種對代現(representation)理念的批判意識。他指出,若用代現的角度來看,「我們大多是在討論文學如何再現一個既成的事實或理念,有時候不免太過拘泥於身份政治——誰是(何為)正港(tsiànn-káng)的,authentic,臺灣人——的範疇。」相對地,不論西方的lyricism,或者中文的「抒情」,都比較重視「無中生有」的興發,從而在起興的過程中去喚起(evoke)某種「新的存在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東西的lyricism,抒情風格,都著眼於存有還未達成的部分,抒情的興發意展現的是「使之成為」、「使之實現」的潛能。
接著,鍾秩維舉例王禎和與舞鶴,這兩位作家都被視為鄉(本)土派大師,批評家多以「混雜性」來詮釋他們的作品。不過,在現行揚舉混雜性的研究取向中,王禎和與舞鶴的寫作頗為倚重的抒情傳統資源——包括詩詞、意(形)象,乃至句法——卻少被觸及。鍾秩維認為,這些作家其實是很有意識地在挪用抒情傳統的元素。比如王禎和在〈那一年冬天〉、〈五月十三節〉,以及〈寂寞紅〉的開篇都引用古典詩歌,顯然有意為之。鍾秩維認為,這些徵引有意思的點在於:「王禎和引用的古典詩歌講述的原來是士大夫的流寓與不遇心事(如杜甫〈宿府〉),或者年華老去的宮娥嘆逝的感傷(如元稹〈行宮〉),但小說家所要說的故事,卻是本土(花蓮)底層民眾的困難生活。」如此一來,王禎和的挪用就不再只是單純的向抒情大師致意,而涉及錯綜複雜的符號轉化。
位移中的文學邊界 青年學者在路上
憶起博士生時期反覆修改論文、發表與投稿的經驗,必經過程就是回應講評、乃至審查意見。鍾秩維認為「思考對方為何有誤解」是一道困難但不可逃避的功課,他解釋道:「對方的指正或誤解都是其來有自,比如我談抒情傳統會收到大量質疑,最常見的比如:難道中國文學只是『抒情傳統』?或者某某作家屬於或不屬於『抒情傳統』?」對此,他認為抒情傳統當然不是歷史的全部,而是一種看待歷史的方式。因此,與其去執著在賴和,或者郭松棻算不算抒情傳統的爭論,不如探問借用抒情傳統的解釋方法,在已成經典(如賴和)、或正在成為經典(如郭松棻)的案例中,我們還能看見哪些前人未見的議題?
探索當然不會止步於此,鍾秩維也持續關注「臺灣文學」與臺大的關聯,在他看來,那一批從《現代文學》發跡的戰後現代派作家,他/她們的實踐對於理解當代文學的狀況仍深富啟示。鍾秩維注意到,當年臺大文學院的課堂會引介西方較新的理論和小說成果,教師鼓勵學生翻譯或寫評論,並從中擇優在《現代文學》上刊載;設若稿量較足,還可以製作成專題;而這些專題中有不少更進一步編輯為專書,由白先勇成立的晨鐘出版社即時發行。這一套「生產鏈」大可被視為臺灣文創的先驅。除此之外,鍾秩維也用心於現代派作家較少被留意到的文本,他參與過李渝文集、研究資料彙編的編輯工作,郭松棻作品與手稿的解讀社群,目前也正與張淑香教授、楊富閔著手整理《沉思與行動:柯慶明論臺灣現代文學與文學教育》,希望藉由新的資料,更多元地描繪臺灣文學與臺大的關聯。
對於寫作習慣,鍾秩維在撰寫碩論時發現自己喜歡「追根究柢」,並且延伸想法的傾向。譬如談論抒情傳統,他會追溯其來龍去脈,以勾勒其背後豐富的可能性。定位自己的調性,從論述過程中摸索個人風格,進而找到適合自己的形狀,這是鍾秩維給研究生的建議。而回望碩、博士期間的試驗與探索後,他認為做一位研究者不只要膽大心細,還要能夠「打開自己,跨出舒適圈,不輕易滿足於現狀。」基於自身經歷與目前國內學術環境的變化,他指出本土博士也可以多方面、跨領域地訓練自己。
觀察研究趨勢,鍾秩維指出,晚近「文學」是什麼的邊界持續在位移,不論西方或華語語系世界都重新思考「文學/literature是什麼」的問題。 照這個脈絡來說,就如文創產業與文學轉譯的話題興起,與此同時,也有學者主張回到古典中尋找新的理論資源。凡此都造就了當代文學研究的多樣性。面對如此眾聲喧嘩的情況,鍾秩維希望能回到本身被「文學」感動的初衷,對他而言,「文學處理的是『溝通』、『界限』,與『愛』的問題。」回返從事學術工作的起點,他察覺自己一直企圖追索的核心問題是「文學是否仍能更新我們對於世界的理解?」秉持這樣的關懷,鍾秩維期待未來的研究能更多元、更深刻地呈現臺灣文學在「世界中」展開的軌跡。
採訪:吳佳鴻(臺大中文博士生)
撰稿:李蘋芬(政大中文博士生)
廣博的學思發展 從政治系到臺文所
今年(2020)甫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的鍾秩維,博士論文《抒情與本土:戰後臺灣文學的自我、共同體和世界圖像》同時獲得臺灣中文學會「四賢博士論文獎」與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文學傑出博碩士論文獎」青睞,備受肯定。
在這本論文中,他以「抒情與本土的相遇時刻」為思考起點,聚焦戰後臺灣文學,考察個案包括王禎和、白先勇、朱天文、李喬、李渝、宋澤萊、邱妙津、楊牧、夏宇、舞鶴、齊邦媛與鄭清文這些分佈於差異的世代、政治意識形態、文學場域習癖、美學流派,乃至性別與性取向光譜上的作家至於文類方面,除了慣見的小說、詩和散文之外,亦處理回憶錄、文學(史)文論、乃至藝術(繪畫、電影等)批評等等的材料,期待藉此能夠對流行於戰後文學場域中的「抒情」和「本土」論述,有全面性的觀察。在方法學上,鍾秩維試圖以跨領域的角度來釐清在「臺灣文學本土論」與「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之交錯和交鋒中,所暗示的華語語系文化如何受容、轉化「中國性」的問題。
現職臺大「趨勢人文與科技講座」博士後的鍾秩維,曾以「侯氏訪問學人」(Hou Family Fellow)的身份赴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交換一年,學術經歷豐富。觀察臺、美學風的相異之處,他發現哈佛學生比較勇於爭取機會、表達想法,在撰寫論文時,除了指導教授,也與committee的成員保持更密切的聯絡,便於在即時的討論中補充、乃至修正論點。同時,「在美讀書的學生似乎也較樂於互相切磋學術觀點,甚至分享材料,我滿欣賞這點,所謂『獨學而無友則孤陋寡聞』,做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對話對象』。」這也與鍾秩維追求深廣的學術取向十分契合。在研究生階段,除了跨系跨領域選修,複雜化自己的學術視野外,他也規律地與跨系所的成員一同舉辦讀書會,主題通常是新興的學術議題,包括視覺文化、華語語系與漢文脈;也會對經典的思想家做精讀,例如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柄谷行人等。他認為讀書會很能激盪不同的觀點,從而多面向地開拓新的研究取徑。
進入臺文所之前,鍾秩維就讀於臺大政治系,系上學風自由,當時他已廣泛接觸社會系、外文系、中文系與歷史系的課程,這些經驗都成為他往後在臺文所展開思辨的基石。研究所期間,恰逢李渝、史書美、白先勇和王德威等海外知名作家、學者,先後應「白先勇文學講座」之邀,在臺文所擔任客座教授。其中李渝、白先勇以及負責該講座的柯慶明教授,均為臺灣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的直接的參與者,鍾秩維碩一時修習李渝「文學與繪畫」、「小說閱讀和書寫」課程,接下來也長期擔任白先勇與柯慶明大學部課程的助教,耳濡目染下,對於那一世代人的文學觀,以至於看待世界的方式特別親切,臺灣現代派遂也成為他博士論文實例主要的取樣對象。
質疑與拓寬 「喚起」世界中的抒情
「抒情」與「本土」,此二看似矛盾的現象,其實具有值得透過比較,來進一步深省之處,就如鍾秩維說起發表於今夏的博論時指出:「我將抒情和本土兩個問題並置,前者上接學者對於中國文學與文化的本質為何的界定,後者是臺灣文學批評家追尋本土國家意識的意圖,它們看似背道而馳的兩種民族主義慾望。」不過,他也指出,追究「抒情」與「本土」論述在戰後臺灣興起的時間,會發現它們都與七、八〇年代一系列內政、外交的壓力息息相關,某種意義上,它們都反映了島民對於什麼是「臺灣人」的身份/認同(identity)焦慮。「本土」作為一種定義臺灣人身份的話語自不待言,鍾秩維進一步提及,「抒情傳統」也是在地對於「中國」文學具有創意的轉化,或可視為臺灣對於中國文學的一種「批判性的繼承」。
循此,面對有關「抒情傳統」不夠「本土」的批評聲音,鍾秩維如此回應:「『抒情傳統』本質上是一個『現代的發明』,它的出發點是『海外』的華人離散社群,而尤其立足於『台灣』。在這個意義上,『抒情傳統』的『現代性』問題,不免也就是『中國古典文化』如何在中國大陸之外的區域,重新被詮釋、被發明的問題,而這個過程透露的,毋寧是某種『花果飄零,靈根自植』的期待。」用當代理論的話來說,他認為這種將關注的焦點會從「中國」本身,移到「非中國」的地方如何接受、新創「中國(性)」的轉向,正標誌出了「華語語系」(Sinophone)研究的起點。
沿著這一問題來說,對於「抒情傳統」以今律古,透過西方來看中國的質疑,鍾秩維首先回顧晚近學界如何回應「何謂中國」的質疑。如許倬雲、葛兆光等學者都已經提出,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中,「中國」何所指的內涵一直處於變動,尤其以「漢字漢文」為基礎發展生成的「中國」文化,古往今來都在「文」與「言」界限的建構和解構之間,反覆釐定何為「他者」,而表述「自我」為何。換言之,「華」「夷」之間不見得壁壘分明,從我們今天的後見之明看來,也未必有孰高孰低的階序。在這個意義上,「抒情傳統」不過是前述歷史長流此時此刻的一種演繹,相對之下,民族主義者排他性的、本質主義式的「中國」定義,反而才真正是以今律古的說法。鍾秩維提到,近來王德威教授借用史學家杜贊奇(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的說法,呼籲 “Rescuing Literature from the Nation”,而認為誠哉斯言。
將話題帶回臺灣,鍾秩維說:「有語言學的研究指出,『臺灣』一名來自西拉雅話中的“Tai-an”或“Tayan”,指『外來者』,從此可見,不只何謂『中國』,就連何謂『臺灣』,答案都指向本土與外來元素不斷協商的動態過程。但這並不等同於我們可以就此逃離民族主義,它畢竟主導了現代以來人類最主要的共同體論述;而是作為人文研究者,我們仍要與它保持一個讓批判得以展開的距離。」這一必要的距離,使鍾秩維跳脫民族主義的框限,對「抒情」與「本土」進行比較研究;此外,此一距離所給予的啟示也能從他在「2020臺灣理論關鍵詞」會議上提出的「笑詼(tshiò-khue)」看出端倪。該研究雖然立基臺灣文學獨特的語體,嘗試鉤沉臺灣人喜感現象的理論暗示,但在理論化的過程中,亦不可能繞過中國與西方對「笑」的理解。畢竟臺灣的語文狀況,一直都在跨文化的流動中混生。
同理,在鍾秩維的臺灣文學研究進程中,除了中文抒情傳統,西方文學與文化理論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參照意義。他注意到在近來有關lyricism和詩歌的理論辯難中,逐漸發展出一種對代現(representation)理念的批判意識。他指出,若用代現的角度來看,「我們大多是在討論文學如何再現一個既成的事實或理念,有時候不免太過拘泥於身份政治——誰是(何為)正港(tsiànn-káng)的,authentic,臺灣人——的範疇。」相對地,不論西方的lyricism,或者中文的「抒情」,都比較重視「無中生有」的興發,從而在起興的過程中去喚起(evoke)某種「新的存在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東西的lyricism,抒情風格,都著眼於存有還未達成的部分,抒情的興發意展現的是「使之成為」、「使之實現」的潛能。
接著,鍾秩維舉例王禎和與舞鶴,這兩位作家都被視為鄉(本)土派大師,批評家多以「混雜性」來詮釋他們的作品。不過,在現行揚舉混雜性的研究取向中,王禎和與舞鶴的寫作頗為倚重的抒情傳統資源——包括詩詞、意(形)象,乃至句法——卻少被觸及。鍾秩維認為,這些作家其實是很有意識地在挪用抒情傳統的元素。比如王禎和在〈那一年冬天〉、〈五月十三節〉,以及〈寂寞紅〉的開篇都引用古典詩歌,顯然有意為之。鍾秩維認為,這些徵引有意思的點在於:「王禎和引用的古典詩歌講述的原來是士大夫的流寓與不遇心事(如杜甫〈宿府〉),或者年華老去的宮娥嘆逝的感傷(如元稹〈行宮〉),但小說家所要說的故事,卻是本土(花蓮)底層民眾的困難生活。」如此一來,王禎和的挪用就不再只是單純的向抒情大師致意,而涉及錯綜複雜的符號轉化。
位移中的文學邊界 青年學者在路上
憶起博士生時期反覆修改論文、發表與投稿的經驗,必經過程就是回應講評、乃至審查意見。鍾秩維認為「思考對方為何有誤解」是一道困難但不可逃避的功課,他解釋道:「對方的指正或誤解都是其來有自,比如我談抒情傳統會收到大量質疑,最常見的比如:難道中國文學只是『抒情傳統』?或者某某作家屬於或不屬於『抒情傳統』?」對此,他認為抒情傳統當然不是歷史的全部,而是一種看待歷史的方式。因此,與其去執著在賴和,或者郭松棻算不算抒情傳統的爭論,不如探問借用抒情傳統的解釋方法,在已成經典(如賴和)、或正在成為經典(如郭松棻)的案例中,我們還能看見哪些前人未見的議題?
探索當然不會止步於此,鍾秩維也持續關注「臺灣文學」與臺大的關聯,在他看來,那一批從《現代文學》發跡的戰後現代派作家,他/她們的實踐對於理解當代文學的狀況仍深富啟示。鍾秩維注意到,當年臺大文學院的課堂會引介西方較新的理論和小說成果,教師鼓勵學生翻譯或寫評論,並從中擇優在《現代文學》上刊載;設若稿量較足,還可以製作成專題;而這些專題中有不少更進一步編輯為專書,由白先勇成立的晨鐘出版社即時發行。這一套「生產鏈」大可被視為臺灣文創的先驅。除此之外,鍾秩維也用心於現代派作家較少被留意到的文本,他參與過李渝文集、研究資料彙編的編輯工作,郭松棻作品與手稿的解讀社群,目前也正與張淑香教授、楊富閔著手整理《沉思與行動:柯慶明論臺灣現代文學與文學教育》,希望藉由新的資料,更多元地描繪臺灣文學與臺大的關聯。
對於寫作習慣,鍾秩維在撰寫碩論時發現自己喜歡「追根究柢」,並且延伸想法的傾向。譬如談論抒情傳統,他會追溯其來龍去脈,以勾勒其背後豐富的可能性。定位自己的調性,從論述過程中摸索個人風格,進而找到適合自己的形狀,這是鍾秩維給研究生的建議。而回望碩、博士期間的試驗與探索後,他認為做一位研究者不只要膽大心細,還要能夠「打開自己,跨出舒適圈,不輕易滿足於現狀。」基於自身經歷與目前國內學術環境的變化,他指出本土博士也可以多方面、跨領域地訓練自己。
觀察研究趨勢,鍾秩維指出,晚近「文學」是什麼的邊界持續在位移,不論西方或華語語系世界都重新思考「文學/literature是什麼」的問題。 照這個脈絡來說,就如文創產業與文學轉譯的話題興起,與此同時,也有學者主張回到古典中尋找新的理論資源。凡此都造就了當代文學研究的多樣性。面對如此眾聲喧嘩的情況,鍾秩維希望能回到本身被「文學」感動的初衷,對他而言,「文學處理的是『溝通』、『界限』,與『愛』的問題。」回返從事學術工作的起點,他察覺自己一直企圖追索的核心問題是「文學是否仍能更新我們對於世界的理解?」秉持這樣的關懷,鍾秩維期待未來的研究能更多元、更深刻地呈現臺灣文學在「世界中」展開的軌跡。
採訪:吳佳鴻(臺大中文博士生)
撰稿:李蘋芬(政大中文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