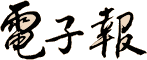殖民帝國下台灣民權運動的歷史意義:一個歷史社會學視野下的解釋──「王詩琅臺灣研究講座」若林正丈教授演
中心動態
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電子報第24期
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電子報第24期
2019-03-29

由臺灣大學文學院與臺灣研究中心合辦的「王詩琅臺灣研究講座」於2019年3月19日假台灣大學普通大樓舉行。本講座邀請早稻田大學台灣研究所所長若林正丈擔任主講人,講題為「殖民帝國下台灣民權運動的歷史意義:一個歷史社會學視野下的解釋」。

 演講開始由台灣大學文學院台灣研究中心主任及臺大中文系系主任梅家玲引言介紹本講座的創立緣起與歷次演講的專家學者,並由台灣大學歷史系呂紹理教授擔任演講主持人。呂紹理先生提及今年距1920年田健治郎提出台灣地方改正將近一百週年,當時其宣稱要為將來台灣地方自治做準備,關鍵卻在「準備」,準備過程十六年間其實相當曲折。這當中並非單純是殖民者的施予,更包含許多在地知識份子社會力量的參與,此也即是若林正丈教授的演講論題所在。
演講開始由台灣大學文學院台灣研究中心主任及臺大中文系系主任梅家玲引言介紹本講座的創立緣起與歷次演講的專家學者,並由台灣大學歷史系呂紹理教授擔任演講主持人。呂紹理先生提及今年距1920年田健治郎提出台灣地方改正將近一百週年,當時其宣稱要為將來台灣地方自治做準備,關鍵卻在「準備」,準備過程十六年間其實相當曲折。這當中並非單純是殖民者的施予,更包含許多在地知識份子社會力量的參與,此也即是若林正丈教授的演講論題所在。



若林教授首先清楚點明本次演講的主旨之所在,是要說明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民權運動,自有其社會背景、運動過程與運動願景,但是要如何思考與探索其中的歷史意義?若林教授認為,可以將這些面向置放在歷史社會學的視野下進行考察。所謂的台灣民權運動,所指的是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及要求實施完整地方自治的運動,而歷史社會學的討論,在演講中則主要涉及Michal Mann關於「政治的力」(political power)的相關理論思維與研究方法。
在演講第一部分「前言」的最開始,若林教授首先引用並肯定了周婉窈教授《少年台灣史》一書中的論斷,周教授總結台灣的近代化(日本對台灣的半世紀統治),是海外版、少掉議會政治的小型明治維新,而由於缺乏議會政治,殖民地民眾對於自身的語言、文化及歷史沒有決定權。
若林教授進一步談到導致殖民地台灣議會政治的缺席的背景,指出當時日本政府「已具備近代國家所必備的的兩項制度:中央集權的理性官僚制以及從地方到中央的議會政治的制度。」對當局而言,雖然體認到長遠而言殖民地的參政權必將成為問題,但整體的治理策略則是先施行同化政策,再依照台灣人民的「民度」考量放寬參政權。這樣的結果,導致殖民時期的台灣,「議會政治」始終未實現。另一方面, 1945年4月開放的中央參政權也因為日本戰敗淪於空談。行政參與層面,台灣人雖有不少能參與「役場」,卻很少能被總督府任用為高等官。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若林教授思考「重訪台灣民權運動」,即1921至1937年台灣人追求議會政治及地方自治的運動。並試圖從不同於周婉窈教授歷史學家的研究方法,對此一問題再次重探。所謂的不同方法,是雙重的歷史社會學途徑。第一層的問題意識,是藉由Michael Mann 「政治的力」的視角作為研究方法,第二層問題意識則是若林教授這幾年逐步建構中、探索「台灣來歷」的研究視角,以「台灣是諸帝國的週邊」為中心命題,通過「方法上的“帝
國”主義」,也就是「帝國之網」與「帝國之鑿」的複合性視角,勾勒關於「台灣來歷」的幾個歷史脈絡,包含「開拓、通商與國家」、「調查與國家」、「民權與國家」、「原住民族與國家」、「〔『一個中國』政治〕的動力學」,藉以刻畫台灣人民如何「在諸帝國的周邊活下去」,甚至回答區域研究的根本問題:「台灣是什麼?」
第一層所引用的Michael Mann 概念出於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Ⅰ-Ⅳ所討論的為「社會的力」,以IEMP模型概括。首先,社會由四種力(power,透過控制自己的環境達成目標的能力,兼指權力與能力)的複合網絡構成,分別為ideological power/意識形態的力;economic power/經濟的力;military power/軍事的力;political power/政治的力。其中,政治的力即為國家權力。關於Michael Mann「政治的力」概念,若林教授指出其中重要的一點為「政治的力」發生作用的社會空間具有「雙重性」。在「國內性空間」,「政治的力」透過中央管理與區劃空間執行,具有領域性與中央集權性,而在另一方面則是「國際性(外交性/地緣政治性)空間」 。這是因為「政治的力」的領域性,使其不得不處理與同樣具有領域性的相鄰組織之關係。如此空間具有外交性與地緣政治性作用。「政治的力」在 「國際性空間」遭遇的壓力或機遇將影響 「國內性空間」,而「國內性空間」內成員的整合程度,也影響其被捲入國家地緣政治的程度。
進一步細談「政治的力」,意即國家權力,在「國內性空間」運作的兩種層次,可分為1.專斷性權力(despotic power)裁決政治決定的權力與2.基礎結構性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IP)執行政策的具體力量與權力。專斷性權力的強弱,主要依照境內是否存在有力的群體,不論是議會、政黨、封建領主、城邦等團體,能夠牽制主要決策的執政當局,使得政府不得不經常與之協商。專斷性權力可能隨著時間的發展減弱,在前現代可能因為地方割據而使得帝國的中央權力崩潰,在現代則可能通過民主化的議會政治或政黨政治,使得國家菁英的權力得到制衡。至於基礎結構性權力,則是國家滲透到社會每一角落,動員、編制所需的資源(人員、物資等)在適當的時間地點讓國家的組織或制度能夠適當的運作,落實國家菁英決策的能力。簡言之,從總督府、警察與醫療制度、交通、教育……等等皆涉及基礎結構性權力的運作。基本而言,隨著時間的推進,基礎結構性權力只會逐步增強。而依據佐藤茂基的整理,基礎結構性權力又具有雙重社會作用及兩面性。其一,整合社會的作用,「power through society」若林教授認為此為Michael Mann基礎結構性權力的討論中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其一整合社會的作用,社會生活與國家權力的關係緊密,加強社會的領域性,也使得國家機構與人員不斷增長,而社會生活愈被捲進國家的制度網絡裡面去;其二,基礎結構性權力具有誘發社會紛爭的作用。首先中央當局通過制度滲透的基礎結構性權力與地方舊勢力產生衝突,而基礎結構性權力導致的社會諸因素之間與社會和國家之間的紛爭,更會催生出對國家制度「有意見的人」,於是權力分配、參政問題皆開始提出並逐步複雜化。
回歸到台灣歷史的觀察,或許可提出一假設,也就是「無代表無課税」這樣台灣民權運動的原理性主張,其實隨著近代性的行政制度的擴張難免不出現。另一方面,日本當局在推進近代化,同時也逐步增強基礎結構性權力時,就已經意識到立憲政治與地方參政權的議題遲早將出現,因而日本政府其抑制殖民地人民參政權的「預防性(proactivity)」非常強,「漸進式的内地延長主義」的官方論述的形成也與此相呼應。
對於民權運動者對於自由的要求,戰前日本殖民帝國與戰後在台的中華民國有其共通點,若林教授稱之為「時間差的邏輯」。意即,面對此刻的民權與自由的要求,皆為立憲主義政體的政府,論理無法直接否定民權,於是改採推遲民權時間點的策略。就日本政府而言,以「先同化再說」的「內地延長主義」政策,認為台灣的民權議題「為時尚早」,並由日本菁英掌握對台灣「民度」的判斷,推遲民權的到來;中華民國政體則宣稱在非常時期,應該以打倒共匪為優先。
但是,這固然是日本當局的立場,但是若從基礎結構性權力的辯證法思考,隨著基礎結構性權力的增強,「有意見的人」的群體也開始於歷史場景中出場。隨著國家制度滲透的基礎結構性權力,在台灣漢人社會中最早接觸此一權力的是本地地主資產階級,或可說是社會領導階層。此一階層對國家制度可能產生不滿、階層中對於國家制度有意見的人容易產生,而形成「有意見的人」的群體,也是台灣民權運動的社會基礎。1910年代可以說是台灣民權運動的前夜,因為雖然有對國家制度的不滿、有民權觀念,但是這些地主資產階層中的「有意見的人」,還是仰賴日本政客、組織鬆散且缺乏明確論述。民權運動仍有待「能組織意見的人」,也就是具有論述性讀寫能力的民權運動者的出現。但是,基礎結構性權力的辯證法就在於,為了增強基礎結構性權力的運作,而推行的教育政策所培養出來的讀寫能力,當然對國家菁英而言,是重要的管理因素,有利於訓練、乃至動員國民資源。但是,讀寫能力不可能專屬於國家,社會成員也可賴以自我培力(empowerment)。論述性讀寫能力(discursive literacy)的普及,會提高社會成員的組織動員能力,甚至生產自己的「政治的力」的可能性,醞釀批判性論述、組織不同意見與政治團體等。另外,對於跨境傳播的思潮與論述的接收反思能力也提高了。在殖民地情境下,這一種具有論述性讀寫能力、雙語能力的知識分子就具有其重要性。1910年代,隨著留日學生逐漸增加、總督府國語學校與醫學生的畢業,具有雙語論述讀寫能力的高學歷新興知識分子階層開始形成,加上一次大戰後新意識形態的跨境傳播,進而在1920年代推動政治、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活動。這一類新興知識分子可說具有三位一體特性,也就是具有殖民地公職經驗、菁英學歷,又同時是民權運動家(報導或演說),他們可說是基礎結構性權力辯證法的寫照,公職經驗催生有意見的人,而通過自我培力再形成有意見的群體。黄呈聰(1886-1963)、楊肇嘉(1892-1967)皆是案例。從林獻堂、黃呈聰聯名向伊澤多喜男總督提出的建白書(1924年10月30日)要求充分呈現「土著」地主資産階級「新興知識人」的政經要求。林獻堂、楊肇嘉亦曾提出民權、司法、義務教育等相關要求,皆是例證。
上述部分,若林教授是以基礎結構性權力與民權運動的關係,以「帝國之鑿」的概念進行陳述。至於觀察台灣民權運動與日本帝國/台灣島的地緣政治,若林教授則以「帝國之網」進行闡釋。空間上來說,與民權運動相關的政治的力運作的社會空間應分三層,M.Mann指出政治的力運作的空間可分為國內性空間與國際性(外交性、地緣政治性空間)而國內性空間又分成殖民地內空間與帝國內空間,因而可分三層。殖民地內空間意味著直接與國家(總督府)面對的社會空間,此以台北為中心。帝國內空間意味控制總督府的帝國政治的力運作的社會空間,以東京為中心。至於帝國際空間,就是日本帝國面對的國際性空間,山室信一稱為「競存體制」,相關概念參照山室信一「『国民帝国』論の射程」。於是,思考台灣民權運動除了三個行動層次,也就是台灣民眾、總督府與帝國中央外,也應該有三層次的比較視野,1.台灣內:在台「內地人」、總督府官僚、警察與「本島人」、2.日本帝國內:殖民母國與諸殖民地以及3.帝國間。若林教授並以概念表及整理表梳理日本與台灣因不同空間層次與治理政策呈現的影響關係。
演講的尾聲,若林教授結合理論的討論與史實的觀察,提出幾點觀察。其一,日本帝國的地緣政治的處境與台灣民權運動的興衰有3點關聯:1.和民權運動興起有間接關係,因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地緣政治對日本帝國有利,得以有效壓制武裝抗爭,因而反抗只能從與國家制度的互動中探索2.直接關係,在日本中央軍部跋扈的歷史情境下民權運動被壓制3.與二戰末期,因為戰局不利而開放中央參政有直接關係。第二點觀察則是,殖民帝國的基礎結構性權力與社會的辯證法式互動,與民權運動興起有直接關聯。另外,一次大戰後跨域意識形態的傳播,也增強了組織意見者的論述組織能力。從上述的討論,也可以為台灣百年民權的發展劃出一條輔助線,觀察「政治的力」的類型與在台灣的國家權力的發展。雖然民權運動在清帝國時期不可能、在日本殖民時期未完成,但長遠來看卻逐步實踐了。
回到最初的論題,表面上,這樣的討論似乎只是再次詮釋既有見解,但是若林教授指出,首先由不同的途徑重新詮釋既有的見解也有其學術意義,其次這提供對國家權力更複雜的想像與思考,實際上國家權力不只是「拳頭」,更是無所不在滲透性的國家機制,最後則是這樣的討論,實際上背後還有更大、仍在建構中的詮釋框架,是若林教授期待往後繼續與聽眾、學界分享的。最後,若林教授亦提出對演講尚未充分解決的問題進行提點。以IP辯證法的詮釋來說,演講聚焦在立法權,但是台灣基層公務人員的行政參與也逐步擴大,這一點應該也納入討論。此外,兵役義務與參政權的關係,也還未在演講中充分探討。又,除了「政治的力」以外,整體IEMP模型是否可以用於研究台灣近代史,也還有待深入研究。若林教授認為,這些問題在他建構「方法上的“帝國”主義」當可能進行進一步探索。演講中,除了各地與會學者嘉賓,也有許多同學參與聆聽,並提出問題。例如詢問相同理論模式,是否可應用於日本於韓國的殖民研究,以及若林教授何以從事台灣研究。對前一問題,若林教授認為應當從韓國研究的專業切入,但應當能從類似理論得到研究助益,而就後一問題,若林教授則指出:對日本而言,出現幾名台灣研究的專家是必然,是誰來擔任則是偶然。這其實正呼應了本次演講的主軸:民權運動者的出現,其實也正是有背後歷史的偶然性與必然性,而從基礎結構性權力的辯證法、政治的力與社會空間的討論,正解釋了促成民權運動的諸多因素。
※整理側記:吳佳鴻(台大中文系博士生)